|
那 水
——家乡的记忆之四
我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依山傍水之地,村子西面是赭山,主要农作物有地瓜、谷子、高粱、棉花、芝麻、绿豆等。赭山下就是用泉水灌溉的万亩良田,村南、村北都是上好的水浇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等。村东是水田,主产明水香稻。 村子西边有一条1966年修建的人工河,叫“三支干渠”,水是从明水眼明泉群(以前叫西麻湾)流过来的。村子大西门外的上山之路建有一座两个桥墩、双向行驶的跨河大石桥,石桥两侧的东西两岸专门用石头垒砌了多层的台阶。每天来此洗衣服、洗家什的村民络绎不绝。特别是每年进入腊月廿后,家家户户都把家里大扫除整理出来的物件和准备过年用的各种菜蔬拿到这里来洗刷,家具、炊具、衣服、猪下货、白菜、萝卜、海带……应有尽有。大家一边清洗着自己的东西,一边毫无约束地大声交谈、说笑,真可谓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村子东边有三条从百脉泉群(以前叫东麻湾)流出并行向北的河流。东边的一条就是著名的绣江河,这是章丘市境内最大的一条河,也被称为章丘的母亲河。因水中翠绿的苲草随水流飘动,波纹如绣而得名。我们当地人称它叫“东河涯(读:yai)”。其河床最深,河面最宽,水流量最大,且碧绿的水草密布,只有成年男人才敢下去洗澡。1952年章丘县政府曾组织在中营东侧的河段修筑了拦河大坝,建造了水利发电厂,周边的村庄都通上了电,后因水流量不稳定而无奈停用、废弃。

西边的一条河面最窄,水流量最小,中段有一大石板搭成的桥叫“金岩桥”。这是妇女们经常在此洗衣服、洗澡的地方。中间的一条河面宽度、水流量居中,中段建有水磨房,有三盘大水磨,村里人都把这里叫做“三盘磨”。每盘水磨都是由磨房、引水道、水轮、磨盘和磨轴等部分组成。河水沿着引水道汹涌而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水轮带动石磨旋转。水磨起初被用来研磨祭祀用的香料(用柏树根、榆树皮等作原料),后来改作磨面粉。在尚未通电的年代,这日夜旋转的水磨,不但节约了能源,而且还是没有污染的环保磨面工具。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东、西两边的水磨已经没有了,只有中间的那盘大水磨。我与小伙伴们经常钻到下面去看那水流冲击木轮旋转的壮观情景。
东南侧的水磨拆除后,由于水势落差的原因,水流湍急,在引水道的东面被冲击形成了一个开阔而很深的大水湾,叫“闸湾”。这是我们这些半大男孩经常在此洗澡的地方。记得我上二年级时的一个下午,李桂珍老师领着我们去洗澡,她组织女同学在“金岩桥”处洗澡,让我带领男同学到“闸湾”处洗澡,两处东西相距约有200多米。那时农村人都不讲究,二十几个男同学,都是脱得赤条条地跳入“闸湾”,有打水仗的,有潜水捉迷藏的,玩得非常开心。我们几个胆大的同学,还站到高高的闸桥上面,学着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样子,高喊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纵身跃起,一头栽入水中,潜泳很远才再钻出水面。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小伙伴彭其昌从闸桥上跳下呛水休克,被水流冲出很远。刘炳新同学首先发现,大喊:“彭其昌怎么了?怎么被水冲远了!”我马上招呼几个同学追过去,把他抬上了河岸。只见他的脸色惨白,没有一点血色,吓得我六神无主。一边安排同学去报告老师,一边呼喊附近干活的村民过来帮助抢救。不一会儿,李老师神情惶惶地赶来了,急乎乎地命令我与韩同荣同学马上回村去叫彭其昌的父母。我俩二话没说,撒腿就向村里跑去。当我俩领着彭其昌的妈妈匆匆赶来,正碰上李老师与同学们正背着已经苏醒的彭其昌向回走。这时我俩才发现各自还都一丝不挂呢,脸一下子就红了,蹲在地上大喊:“我们的衣服呢?”刘立婷同学在老远处回答:“我给你们拿着呢!”说着就把我俩的衣服送了过来,我们这才急匆匆地穿上了衣服。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总是觉得既后怕又好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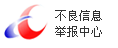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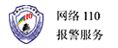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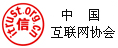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