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每个人生命中印像最深的莫过于自己的家乡,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否功成名就,都不会忘记那片生养自己的故土。每当提起家乡,总会有回味不尽的儿时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记忆,愈发清晰,常常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 我的家乡——山东省章丘市明水街道办事处西营村,位于“小泉城”明水以北三公里处,依山傍水,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村大风淳。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二十三年时光。家乡给了我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感受,那村、那人、那山、那水、那学校、那……无不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 那 村 ——家乡的记忆之一 我的家乡西营村,南邻浅井村,北邻宫王、牛王村,西靠赭山,东与前营、后营、中营三村几乎连成一片。由于四个自然村落早已经形成相互连接、交错的状态,外乡人很难分辨出其明确的界限,故将其统称为四营(或称营里)。 史传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声势日趋壮大。汉献帝建安七年,袁绍病逝,曹操审时度势,挥师北伐,多路大军齐头并进,每路都分成前、后、中、西、东五个大营。大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于建安九年,攻取袁氏的根据地邺城,次年又击杀袁绍长子袁谭,其弟袁尚、袁熙逃奔辽西投靠乌桓。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虚国而征”,率二十万大军、数千辆战车、文臣武将中几乎所有的精锐北上讨伐,彻底消灭袁尚、乌桓联军,统一了中国北部。战争结束,曹操为安定北方,将大军仍按原军营编制,选择依山傍水之地屯田开发,闲时为民,务农生产,战时为兵,操刀上阵。经年累月,繁衍生息,在中国北方形成了众多以“营”为名的村落,我的家乡就是其中的一处。开始为前营、后营、中营、西营和东营五个村落,由于东营地处低洼之地,经常遭受洪水的侵袭,其幸存者便逐步西迁并入上述四营,于是只剩下前、后、中、西四个营的自然村。 我儿时的西营村,是四个营中村落面积最大、经济最富、人口最多的村庄。村落整体为矩形,南北长,东西短,高大、雄伟的围子墙绕村一周,从西边的赭山上远远望去犹如一座灰褐色的大型城堡。村中贯穿南北的道路只有一条,称作“大街”,把村子几乎对称式地分为东西两片。可别小看这“大街”,它可是当年横贯章丘南北的主要交通要道,每天可谓车水马龙。站在大门口看过往的骡马大车,就是儿时我与小伙伴们的乐趣之一。在村子北部“大街”路西和路东各有一个车马店,在村子南门外还有一个很大的车马店,三个车马店几乎每天都是客满。“逢二遇七”的集市也是设在这“大街”上,十里八乡的小商贩和购物者汇聚而来,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煞是热闹。村中贯穿东西的道路只有两条,北面的叫作“西沙沟道”街和“东沙沟道”街(两街不直通,南北相错约70米);南面的叫作“小西门里”街和“小东门里”街。在“西沙沟道”街和“小西门里”街之间,有一条“小胡同”。在其西头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区域,叫作“解元巷”。因刘家麟在清朝嘉庆二十一年以山东乡试第一名中举人,获解元称号而命名。在“小西门里”街南面,还有 “大胡同”和“新大门”胡同。在“大街”南段东侧、“小西门里”街和“小东门里”街之间,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场地,因其形状像蝎子,称作“蝎子湾”,后又称作“湾涯(读:yai)”,这可是当年听说书、闹扮玩、看演戏、观电影的主要场所。 据村里老人讲,西营村开始时村落是比较小的,只有西北方“大街”以西、“西沙沟道”街以北的部分。后来由于人口繁衍和外来定居者不断增多,才逐渐扩大,形成了人口众多、面积庞大的村落。其实,在我童年的时候,即便在围子墙以内,也还有西北侧的“坟园后”、东北侧的“公鸡坟”、东南侧的“北园”和“南园”等大片空地,1976年以后才逐步被新批宅基地,建成了新的住宅区。 儿时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莫过绕村一周的围子墙。围子墙南北长500多米,东西长300多米,正南正北整体呈矩形,只有两处拐弯。一处是在西北段、九女碑南侧向东折弯约30米;另一处是北门东侧向南折弯约20米;两处均形成九十度的拐角。围子墙主墙高约8米,顶端外侧筑有约1.5米高、20公分厚的垛墙,每个垛墙的上部留有方形的瞭望孔,用于隐蔽观察和射击使用。内侧筑有高约1米、厚约20公分的宇墙,以防巡逻人员跌落。垛墙与宇墙之间的通道宽约1.5米,可供两队人员自由相向而行。垛墙与主墙顶部表面接壤处设有悬眼,主要是用于雨期排水保护墙体免遭水泡,亦有阻敌登墙的作用。围子墙底部基座宽约5米,高约1米,用石块灌搽灰(石灰与黄土混合搅拌而成)砌成。主墙体由外檐墙、内檐墙和其之间的填充层三部分构成。内、外檐墙厚度约50公分,用黄土、石灰、粘土和水搅合后浇注而成。浇注时,有明显的收分(底部宽,向上逐渐收缩),以增强墙身的稳定程度。据村里老人传说,建围子墙时,每隔50米就树立一副顶端安装有滑轮的支架,使用绳索吊住条编抬筐、或者大铁桶,向上运送已经搅拌好的混合灰浆和填充用的黄土、石灰粉等。浇注外檐墙时,用稻草将长长的芦苇绑成把子,横担在已经浇注成的檐墙上,两端插进模板上预留的圆孔中,将两页模板吊挂在已经浇注成的檐墙两侧,然后将搅合好的混合灰浆浇注到两模板之间,并震动搅拌匀实。等凝固后,摘下模板,将伸出檐墙外的芦苇剪掉。内、外檐墙中间用黄土填充,并撒上石灰粉,用锥形、平底杵头等逐层夯实。就这样一版一版地建造,每版厚约30公分。 在围子墙上设有六个门,“大街”北头的叫北门,南头的叫南门;“东沙沟道”东头的叫大东门,“西沙沟道”西头的叫大西门;“小东门里”街东头的叫小东门,“小西门里”街西头的叫小西门。每个门两侧用石块垒砌,顶端为石拱碹砌而成。拱门上方的门额正中镶嵌着一块矩形青石,上面写有两个凹刻魏碑体大字,分别是:南门——炳文;北门——承恩;大东门——秀水;大西门——赭山;小东门——迎旭;小西门——晚霞。每个门口一侧建有3米见方、与围子墙主体等高的筑台,地面有通向筑台的台阶蹬道。筑台上方建有青砖角楼,里面有土炕,供值更人员使用。大门门板用厚约6公分的榆木板制成,每扇高约3米,宽约2米,门扇后边有锁门用的铁门鼻子、门栓和粗壮的腰杠。一到天黑值更人员就关门上锁,插上腰杠,来人未经允许不能进入。 据村里老人传说,当年建造围子墙主要是用来防水、防盗和防匪。围子墙建成后,村里的青壮年统一安排,轮流值更,每个门口都有人把守,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那时,村里人开会下通知,都是有关人员手持用白铁皮制作的喊话筒,沿着围子墙喊上一圈。 建国后,天下太平,围子墙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利用价值,不再被人们重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围子墙也被当作“四旧”看待,随着扩建房屋逐渐被拆除,很快完全消亡在历史的尘埃里不见踪迹。只留下北门里、南门外、大东门外,小西门里等等习惯性的地域名称。 据南门门额正中镶嵌的“炳文”石刻左下方的小字石刻记载,我村的围子墙于清朝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建成,至今146年。我儿时听老人传说,当年确定修建围子墙后,曾经先后派人到老章丘城(绣惠)以西的旧军村去考察了孟家于明末、清初年间修建的围子墙,到相公庄考察了于清朝咸丰十年修建的围子墙,吸取了两个村子围子墙设计的长处、建墙的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村建造的围子墙比旧军村和相公庄的更高、更厚、更坚固、更实用。
当年建造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围墙工程,肯定占用耕地不少,需要时间不短,耗费人力、物力不菲,组织协调不易。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倡导组织者和实力雄厚的经济基础,那是不可能完成的。据我所知,章丘境内建有围子墙的村镇屈指可数,邻近的县城有围子墙的也不多见,足见建墙工程之艰难。然而我村非县非镇非乡的治所,却能够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建成这么一座宏大的围子墙,足以说明当年的西营村人多势众,团结凝聚,财力雄厚。 村子南门外东侧的车马店,村里人都称作“南店”,是刘氏八世公锡田在清朝末年建成的,是村里三家车马店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占地面积约10余亩,东片是纸坊(造纸厂),西片是车马店。西边的沿街房是饭店、理发店等。解放后,大队先后在里面建成了草绳厂、油坊、饲养院、农校、小学、大队部、电磨房等等。 还有村里四家财主家的高大台屋,北门里“大街”东侧的土帝庙、“西沙沟道”与“大街”交叉口西南侧的刘家家庙、“东沙沟道”北侧路西的李家家庙,村外西北侧元朝年间用青石建造九层塔身的“九女碑”与椭圆形的大水井、舍墓田和两个无名烈士墓,村北侧高高的柏树林与石人、石马、石羊等等,都给我儿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现在西营村的摸样与我儿时的记忆已经是大相径庭,村子建筑面积扩大了一倍多,房屋全部翻新,以前那种土胚墙、麦秸顶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全部被新建的砖瓦房屋所替代,二层的别墅式楼房也比比皆是。1976年村两委还组织在村子东南侧建成了“绣江商贸城”,盖起了五层的公寓楼四座,160户村民已经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居住。

补充内容 (2014-12-11 14:38):
西营村公寓应该是1996年建的,文中误为1976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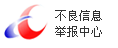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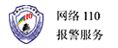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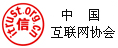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