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зңӢз”өеҪұ 70е№ҙд»ЈеҲқпјҢеңЁеҶңжқ‘зңӢз”өеҪұжҳҜе…Қиҙ№зҡ„пјҢд№ҹжҳҜеҘўдҫҲзҡ„гҖӮжҲ‘жҳҜиҝҷд№Ҳи§үеҫ—гҖӮ дәәж°‘е…¬зӨҫпјҲзҺ°еңЁеҸ«вҖңй•ҮвҖқпјүзҡ„з”өеҪұж”ҫжҳ йҳҹиҰҒжқҘжқ‘йҮҢж”ҫз”өеҪұдәҶгҖӮеҮ еӨ©д№ӢеүҚе°ұиғҪеҗ¬еҲ°ж¶ҲжҒҜпјҢдёҚзҹҘи°Ғиҝҷд№ҲзҒөйҖҡгҖӮ ж”ҫжҳ зҡ„ең°зӮ№е°ұеңЁжҲ‘们еӯҰж ЎгҖӮ еӯҰж ЎжңүдёӘеӨ§жҲҸеҸ°пјҢжҳҜжј”еҮәе’ҢејҖеӨ§дјҡз”Ёзҡ„гҖӮ жқ‘йҮҢзҡ„йқ©е‘Ҫе®Јдј йҳҹдёҚж—¶дјҡеңЁеҸ°дёҠжј”еҮәпјҢе…ЁжҳҜвҖңйқ©е‘Ҫж ·жқҝжҲҸвҖқгҖӮд»Җд№ҲзҷҪжҜӣеҘігҖҒзәўиүІеЁҳеӯҗеҶӣгҖҒзәўзҒҜи®°зӯүзӯүпјҢеҘҪеӨҡеҘҪеӨҡгҖӮжңүзҡ„йғҪзңӢдәҶеҘҪеҮ йҒҚпјҢиҜҙе®һиҜқзңӢеҫ—жңүдәӣеҺҢеҖҰдәҶгҖӮиҝҳжҳҜзңӢз”өеҪұиҝҮзҳҫпјҢзү№еҲ«жҳҜвҖңжү“д»—вҖқйўҳжқҗзҡ„гҖӮ дёҙиҝ‘еӮҚжҷҡпјҢж”ҫжҳ йҳҹжүҚз”Ёе°ҸжҺЁиҪҰиҪҪзқҖеҷЁжқҗжқҘеҲ°гҖӮ жҲҸеҸ°дёҠжһ¶жңүдё“й—ЁжҢӮеҪұеёғзҡ„жңЁеӨҙж”Ҝжһ¶пјҢеӨ§е–ҮеҸӯд№ҹжҢӮеңЁдёҠйқўпјҢиҝһдёҠз”өзәҝпјҢжһ¶еҘҪжңәеҷЁпјҢеҚЎдёҠиғ¶зүҮпјҢеӨ©д№ҹж“Ұй»‘дәҶгҖӮ еҪұеёғеӣӣиҫ№жҳҜй»‘иүІзҡ„пјҢдёӯй—ҙжҳҜй“®зҷҪзҡ„еёҶеёғгҖӮе–ҮеҸӯжҳҜй»‘иүІзҡ„жңЁеӨҙз®ұеӯҗпјҢеЈ°йҹіеҘҪеӨ§пјҢзҰ»еҫ—иҝ‘дәҶеҸ«вҖңйңҮиҖіж„ҲиҒӢвҖқгҖӮ йҰ–е…ҲжҳҜе®Јдј зүҮзүҮж®өпјҢжңүеҶңдёҡзҹҘиҜҶгҖҒз”өзҡ„еёёиҜҶзӯүгҖӮжҺҘзқҖжҳҜвҖңж–°й—»з®ҖжҠҘвҖқпјҡжҜӣдё»еёӯгҖҒе‘ЁжҖ»зҗҶдјҡи§ҒдәҡйқһжӢүжңӢеҸӢпјӣжҹҗең°зҡ„зӨҫе‘ҳиғҶеӨҡеӨ§дә§еӨҡй«ҳпјҢеҸҲвҖңж”ҫдәҶеҚ«жҳҹвҖқпјӣжҹҗең°е·ҘгҖҒеҶңгҖҒе•ҶгҖҒеӯҰгҖҒе…өжҺҖиө·еӯҰд№ жҜӣдё»еёӯи‘—дҪңзҡ„зғӯжҪ®гҖӮеӯ©еӯҗе№ҙеІҒпјҢеҜ№ж—¶дәӢдёҚж„ҹе…ҙи¶ЈпјҢеҸӘзӣјзқҖеҝ«еҝ«ејҖжј”жӯЈзүҮгҖӮ дёҖиҲ¬з”өеҪұжҳҜ4зӣҳжҳ еёҰпјҢдҫқж¬ЎжӣҙжҚўж—¶пјҢдёӯй—ҙдјҡеҒңйЎҝдёҖеҲҶжқҘй’ҹгҖӮж”ҫжҳ е‘ҳж“ҚдҪңеҫҲзҶҹз»ғпјҢе°Ҷз©әзӣҳеҚЎеңЁеҗҺйқўпјҢж–°зӣҳеҚЎеңЁеүҚдёҠйғЁгҖӮе…ізҒҜеҗҺпјҢдёҖжқҹдә®е…үе°ҶеҪұиұЎдј еҲ°дәҶеұҸ幕дёҠгҖӮж•…дәӢеҸҲжҺҘзқҖејҖе§ӢдәҶгҖӮ жңүеҮ з§Қжғ…еҶөжңҖжү«е…ҙгҖӮдёҖжҳҜеҗ¬еҲ°иҷҡеҒҮзҡ„ж”ҫжҳ ж¶ҲжҒҜгҖӮзӣјдәҶеҘҪеҮ еӨ©пјҢж”ҫжҳ йҳҹж №жң¬жІЎжқҘпјҢеҺҹжқҘжҳҜжҹҗдәӣдәәзҡ„жҒ¶дҪңеү§пјҢз”ҹж°”пјӣдәҢжҳҜдёӢйӣЁгҖӮж”ҫжҳ и®ҫеӨҮе’ҢзҲ¶иҖҒд№ЎдәІйғҪеңЁйңІеӨ©пјҢдёӢиө·йӣЁжқҘз”өеҪұж №жң¬ж”ҫдёҚжҲҗпјҢж— еҘҲпјӣдёүжҳҜеҒңз”өгҖӮзңӢеҲ°е…ҙеӨҙеӨ„пјҢеҝҪз„¶ж— еҪұж— еЈ°дәҶпјҢжү«е…ҙпјӣеӣӣжҳҜвҖңзғ§зүҮеӯҗвҖқгҖӮйӮЈж—¶ж”ҫжҳ жңәиҫғзҺ°еңЁиҗҪеҗҺпјҢеҠЁдёҚеҠЁе°ұзғ§иғ¶зүҮпјҢеҸҜиғҪжҳҜжё©еәҰеӨӘй«ҳеҜјиҮҙзҡ„еҗ§гҖӮйҮҚж–°жҺҘдёҠеҗҺпјҢдёҖж®өзІҫеҪ©зҡ„зүҮж®өе°ұеҲ жІЎдәҶпјҢйҒ—жҶҫпјҒ еҪ“然пјҢзңӢз”өеҪұзҡ„дҪҚзҪ®еҫҲйҮҚиҰҒпјҢжҲ‘иҝҷд№ҲжғігҖӮ жҷҡдёҠж”ҫз”өеҪұзЎ®е®ҡж— з–‘дәҶпјҢжӯЈеңЁдёҠиҜҫзҡ„жҲ‘пјҢеҝғжҖқж—©е·ІдёәеҚ вҖңең°зӣҳвҖқиҖҢеҲҶзҘһдәҶгҖӮдёҠеҚҲиҜҫй—ҙжҠ“зҙ§и·‘еҲ°жҲҸеҸ°еүҚпјҢз”ЁзҹіеӨҙеҲ’еҮәвҖңең°зӣҳвҖқгҖӮеҘҪдҪҚзҪ®еҚ жҷҡдәҶе°ұи®©еҲ«дәәеҲ’еҚ дәҶпјҒ дҪҚзҪ®еә”еңЁдёӯй—ҙдё”дёҚиҝңдёҚиҝ‘пјҢиғҪеҚ еҲ°зҙ§жҢЁж”ҫжҳ жңәзҡ„дҪҚзҪ®жңҖдёәзҗҶжғігҖӮ еҰӮжһңи°Ғзҡ„иҫ№з•ҢдёҺжҲ‘зҡ„йҮҚеҸ дәҶпјҢе°ұдјҡжңүдёҖеңәйўҶеңҹд№ӢдәүпјҢжңүж—¶иҝҳеү‘жӢ”еј©еј е‘ўпјҒ дёӯеҚҲж”ҫеӯҰеҗҺпјҢд»Һ家йҮҢжүӣжқЎеҮіеӯҗпјҢж‘ҶеңЁиҮӘе·ұзҡ„ең°зӣҳдёҠпјҢдәҶеҚҙдәҶжҲ‘еҘҪеӨ§еҝғдәӢвҖ”вҖ”йўҶең°з»ҲдәҺзЎ®е®ҡгҖӮ жҷҡдёҠеҗғе®ҢйҘӯпјҲд№ҹе°ұжҳҜд»“дҝғеҷҺеҮ еҸЈпјүпјҢжӢүзқҖзҘ–жҜҚе°ұеҫҖеӯҰж Ўи·‘пјҢжҜҚдәІзҙ§и·ҹе…¶еҗҺеҲ°жқҘиҗҪеә§гҖӮ иҝҷжқЎеҮіеӯҗжңүдәӣе№ҙеІҒдәҶпјҢеҸӨж°”иҖҢеЈ®е®һгҖӮдёҠж¬ЎеӣһиҖҒ家пјҢеҗ¬жҜҚдәІиҜҙе·Іе°Ҷе®ғеҸҳеҚ–дәҶпјҢжҲ‘еҶ…еҝғдёҖйҳөй…ёжҘҡгҖӮ еҮіеӯҗжӯЈеҘҪеқҗзҘ–жҜҚгҖҒжҜҚдәІе’ҢжҲ‘дёүдёӘдәәпјҢжҜҸж¬ЎзңӢз”өеҪұйғҪжҳҜиҝҷз§ҚзЁӢејҸгҖӮзҘ–зҲ¶д»ҺжқҘдёҚзңӢз”өеҪұпјҢ家йҮҢзҡ„е…¶д»–дәәиҮӘи°ӢеҠһжі•и§ӮзңӢгҖӮ еҰӮжһңеҖҹзқҖеҫ®ејұзҡ„зҒҜе…үпјҢз«ҷиө·иё®и„ҡеӣӣе‘ЁзҺҜйЎҫпјҢиҜҙдәәеұұдәәжө·жңүдәӣеӨёеј пјҢдҪҶе…Ёжқ‘зҡ„з”·еҘіиҖҒе°‘жқҘдәҶдёҚе°‘пјҢеҸҜиғҪиҝҳжңүдёҙжқ‘зҡ„д№ЎдәІгҖӮдёӯй—ҙеӨ§зүҮжҳҜвҖңйӣ…еә§вҖқпјҢдҫ§йқўе’ҢеҗҺйқўзҡ„йғҪз«ҷз«ӢзқҖпјҢеүҚйқўзҡ„д№ЎдәІжӣҙжҳҜеёӯең°иҖҢеқҗпјҢд№ҹжңүиғҶеӨ§зҡ„зҲ¬дёҠж ‘е’ҢеўҷеӨҙпјҢйӮЈйҮҢжІЎжңүйҒ®жҢЎ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зңӢзқҖеҪұеғҸе°ҸзӮ№гҖҒеҗ¬зқҖеЈ°йҹіејұзӮ№зҪўдәҶгҖӮ еҪұеұҸзҡ„еҸҚе…үз…§еңЁжҜҸдёӘд№ЎдәІжңҙе®һзҡ„и„ёдёҠпјҢйӣҶдёӯзңӢиө·жқҘз»ҷдәәд»ҘеҠӣйҮҸгҖҒйңҮж’јзҡ„ж„ҹи§үгҖӮ ж•ҙдёӘеңәең°жӮ„ж— еЈ°жҒҜпјҢеӨ§дјҷе·Іжә¶е…ҘеҲ°з”өеҪұзҡ„жғ…иҠӮдёӯеҺ»дәҶгҖӮ еңЁжҲ‘дҫқдҫқдёҚиҲҚж—¶пјҢз”өеҪұжҲӣ然结жқҹгҖӮ ж•ЈеңәеҗҺпјҢеңЁдј—дәәзҡ„е–§еҡЈеЈ°е’Ңй»‘жҡ—дёӯпјҢжҲ‘й»ҳй»ҳи·ҹеӨ§дәәиө°зқҖпјҢеҝғйҮҢеҸӘжңүдёҖдёӘжңҹзӣјпјҡдёӢж¬Ўж”ҫжҳ йҳҹж—©зӮ№иғҪжқҘгҖӮ д»ҘеҗҺпјҢдёҠдәҶдёӯеӯҰпјҢжҲ‘еҜ№з”өеҪұиҝҳжҳҜеҫҲзғӯиЎ·гҖӮ дёҙиҝ‘еҮ дёӘжқ‘зҰ»е®¶еӣӣгҖҒдә”йҮҢең°иҝңпјҢжҜҸж¬Ўж”ҫз”өеҪұжҲ‘йғҪж‘ёй»‘еҺ»зңӢгҖӮ еҲ°зҺ°еңәж—¶з”өеҪұж—©е·ІејҖе§ӢпјҢжӣҙжІЎжҲ‘зҡ„дҪҚзҪ®пјҢеӣ жІЎжңүдәҶжҲ‘зҡ„вҖңең°зӣҳвҖқгҖӮиҝҷж—¶е°ұи·‘еҲ°еҪұеұҸеҗҺйқўи§ӮзңӢгҖӮдҪҚзҪ®д№ҹз®—дёҚй”ҷпјҢеҸӘдёҚиҝҮжҳҜеҪұеұҸдёҠдәәеҫҖе·Ұи·‘пјҢжҲ‘зңӢзқҖжҳҜеҫҖеҸіи·‘гҖӮе—ЁпјҢйғҪжҳҜи·‘пјҢз®Ўд»–еҫҖе“Әи·‘пјҢеҸҚжӯЈдәәзү©зңӢеүҚйқўзҡ„дҪ зҡ„еҗҢж—¶пјҢд№ҹеңЁзңӢеҗҺйқўзҡ„жҲ‘пјҒиғҪж¬ЈиөҸеү§жғ…е°ұжҳҜдәҶгҖӮ з”өеҪұз»ҷжҲ‘з«Ҙе№ҙеўһж·»еҝ«д№җгҖӮйӮЈж—¶жҲ‘жңҹзӣјпјҢжӯӨж—¶жҲ‘з•ҷжҒӢпјҒ 2012е№ҙ5жңҲ2ж—Ҙжҳҹжңҹдё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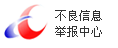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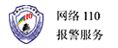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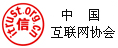
![]()
![]()
![]()
![]()
![]()
![]()
![]()
![]()